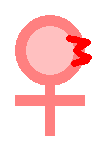
女聲
Woman’s Voice
網址: http://www.south.nsysu.edu.tw/wov/
讀者意見或投稿請寄至:
依瑪貓 imacat@mail.eranet.net
小招 wandy@ms15.url.com.tw
本期文章:
三十歲,未婚女人的政治立場
小招我是一個 30 歲的未婚女人。
不要小看所有 30 歲的未婚女人,她們必須面對在 30 歲後如潮湧來的種種社會壓力。
這絕對沒有年齡歧視的意味。
在父權社會中,只要是一個女人,打從她出生,所有社會對女人的壓迫都逐漸像千層派一樣,層層疊疊地堆上身來,只是裡頭的餡有粗有細,有濃有淡,有酸有苦的分別罷了。
當然,會有所謂的天之嬌女(不論是自封的,或是他人想像建構來的),認為打小貼到身上來的幸福(壓迫)都是甜如蜜的。那很好,我們沒必要讓所有女人都認為自己患了受迫害妄想症
,但我們也不希望所有女人都抱持著打是情、罵是愛
的幸福妄想症
。
我只是想說,女人所受的壓迫是不分年齡階級的,當然,它會有差異。
例如,當一位總統夫人獨自走在夜晚的窄巷裡,她所面對的心理恐懼,不會低於一位剛從工廠上完夜班的女工所承受的。她比這個女工佔優勢的是,她身邊總會有不少的隨身便衣警衛保護安全,但是,如果這位總統夫人落單了呢?這是所謂的護花使者論
。我當然反對。叫大野狼去恐嚇小紅帽,小紅帽唯有委身獵人,才得安全。誰看不出來這是野狼與獵人狼狽為奸,引小紅帽入甕的詭計?
真正的問題是,不管是總統夫人,還是人微言輕的女工,只要她是一個女人,她就沒有行動自由。
似乎離題遠了。我要回頭來講三十歲未婚女人所面對的社會壓力、社會困境、經濟困境、情慾困境……,妳可以將 30 歲替換成各種年齡,所面對的壓力、困境加上種種的形容詞,讓我們招(召)換(喚)各種不同的女人聲音吧!
因為我 30 歲,我的想像力也有限,因此就拿我自己當討論的個案吧!我說過了,我沒有年齡歧視的意思,也沒有矮化其她女人的意味,妳可能會在我身上看到其她女人的影子,我還是必須強調,如有雷同,純屬經驗
。
一般人總認為 30 歲的女人好像很有錢,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坊間的暢銷書告訴女人如何在 30 歲前購屋
,可是,縱使我在大學中工作,又兼一、兩個小教職,要買房子好像是天方夜譚。講難聽點,付完了房租、生活費,我連頭期款都拿不出來,就算頭期款只要 5 萬元,更何況是之後必須長期抗戰的貸款呢!想去申請便宜一點的房屋貸款,對不起,那是嘉惠合法夫妻的。三十而立
,買房子行不通,我開始盤算我的財產繼承權。看看家人都已經幫我盤算好了。我的房子呢,是和我未來的配偶連再一起的。不管是爸爸媽媽、哥哥姊姊都問,男朋友家有沒有房子?
沒有房子?!家人都勸我趁早分了吧!理由是不忍心看我得為房子打拼、吃苦,女兒栽培到這麼大,當然得找個有房子的好人家,別吃虧了。財產繼承權?簡單兩個字:放棄
。連提都不用提。
對女人而言, 30 歲,是一個老化的象徵,這不只是馬齒徒長
的現象而已。妳想想,在大學校園中,如果大四等同沒人要
的話,年屆 30 ,可就是超級沒人要了。不過,不嫁也沒什麼,我既不物化自己,也還養得活自己,人生不是七十才開始嗎?我還不到開始的時候呢。這可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咧!不結婚犯法嗎?當然不。但結婚總是一個合法的制度,一個合法的制度,大家都進的去,妳如果不進去,那麼妳不是有寡人隱疾,就是沒人要。我自己不覺得什麼,家人可把它當莫大的恥辱。在這個社會中, 30 歲,未婚
,早就是一項天大的污名,電視名嘴早已名之單身公害
。父母甚至會用沒把妳教好,所以妳嫁不出去的道德觀譴責妳,也譴責她們自己。將婚姻視為享受人生的入口,人們開始把各種同情的眼光丟給妳,同情妳沒有合法的護花使者,同情你無法享受性的愉悅(所以背後稱妳為老處女),同情妳沒有養幾個小孩子來承歡膝下、享受天倫之樂
,同情社會上又多了一個無人送終、孤獨無依的老女……,不管你願不願承受,這些自以為是的同情像是無厘頭電影中的蘋果派從四面八方炸過來。
相愛的人一定要有婚姻制度來證明相愛
的合法性,否則,就是不倫
。好大的帽子呀!一個女人不結婚就等於放棄了相愛
的權利。為什麼?很簡單,人家會告誡妳,不管對方年紀比妳大、比妳小,女人若不結婚,就別耽誤別人,人家可是要傳宗接代的。好啦,告訴妳對方也是不婚族,我倆只想同居,別人的眼光不止同情,還得加上憐憫了。沒結婚,就和人家住在一起,發生關係,這不注定虧大了? 30 歲的未婚女子若生了幾個孩子可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了。君不見代理孕母
草案都有未婚歧視嗎?要求已
婚才夠格擔任代理孕母。所以不論一個未婚女子多會生孩子,生育能力就是會遭到否定,也難怪已婚不孕(兒子)者的壓力有多大了。
一個 30 歲的單身女子,不論之前有多少情人, 30 歲,未婚
就足以構成一個社會歧視的事實──妳沒有能力綁住一個男人。因此 30 歲未婚的女子事業有成與否並不重要,有不少朋友已經誓死無所不用其極地要把自己嫁出去。托人介紹,或在婚姻介紹所中投注大把的錢,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比較不爛的男人來嫁,最起碼,不用再面對別人知道妳年齡時抱歉的眼神。運氣差一點的,可能遇到的婚姻騙子,成為報紙社會版上的一篇小故事,讓讀者引為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,但這些好事的讀者們除了笑妳傻外,可從來不會認為他們可能是壓迫別人走入婚姻的共犯。嫁不出去
成為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,開始攬鏡自憐,想像出自己身上各種阻撓自己未婚的缺陷
,答案也許是身材太胖、胸部不夠挺、臉蛋不好看、個性不夠溫柔……,不管是什麼答案,總之嫁不出去
都要怪自己改造不夠
。婚姻
轉化為未婚女子心頭自虐的枷鎖。
不斷有人問:為什麼不結婚?
我也常常反問對方:為什麼要結婚?
結婚不過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,一個傳承、確認子嗣的社會制度,從來就不是為了愛情而存在的,在台灣,成年情侶取得婚姻自主權是20世紀初的事。曾幾何時,婚姻成了雙方對感情負責任的作法。確認婚姻上的名分,並不保證會有一個幸福的婚姻生活,讓小孩有父親、母親,也不代表孩子就能快快樂樂的長成。
我, 30 歲,不婚,沒有房子,和愛人住在一起與婚姻制度戰鬥。
女性主義邊地發聲
依瑪貓 26 歲了,我已經習慣用戰鬥
來稱呼我自己的生活。
五年來,早已經習慣了。生活,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戰鬥。不管面對的是家人,還是情人、社團、網友、警察、同事。日子由一場一場的鬥爭堆砌起來。權力的遊戲既充斥在街頭,也充斥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
這樣的我,一旦停下腳步,就會變得很害怕。
我很害怕,害怕寫不出東西。論述的書寫,似乎擺脫不了二元論的陷阱,必然要存在一個對抗的對象,主體才得以存在。我試著擺脫二元論,試著憑空書寫,卻發現失了焦,失了對象。然後就開始習慣性的長期頭痛,腦袋一片空白。
我太 energetic(精力旺盛)了。在不知不覺中,逐漸變成《行動革命》中的葛蘿莉亞‧史坦能(我似乎老是會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自己崇拜的形象),永遠有用不完的精力,在任何事情上。不論在失意的朋友面前,在 BBS ,在椰林拉子板板面上,在女聲的先期製作過程,永遠都有用不完的熱情和精力,陪失戀網友聊天 ,和沙豬筆戰,思考如何塑造拉子板的方向和可以辦的活動,開拉子聊天室,學 Perl/CGI ,寫網頁,寫程式。
史坦能在《行動革命》中說,精力旺盛,是自我空虛的象徵。不敢面對荒蕪的自我,不斷找事來填補自己的空乏。
沒錯。好朋友在文學板辦創作比賽來邀稿,每個月總有一兩個看過我網頁的人,寫 E-Mail 問我什麼時候寫新的詩。我不敢寫。其實是寫不出來。一坐在螢幕面前面對自己,腦袋就一片空白。於是,頂多量產一些村上春樹調調的爛詩,更慘的時候連村上春樹都及不上,淪為流行歌的歌詞。
我害怕,害怕寫不出女聲,害怕自己會被每天的戰鬥淹沒,害怕寫不出自己。
這兩天,臺北市的小學生禁止戀愛了。
一對小學六年級的情侶,因為在午休時間親嘴而引起軒然大波。社會各界交相指責連兒童也被污染了,校長對外澄清該女生還是完整
的,超視新聞字幕就乾脆寫還好女生還是完璧
。
看到這裏,腦子開始暈眩。似乎婦運這幾年的努力都是白做了。記得很早以前唸過 Andrew Rich 的一段話:我們的社會不給女人和小孩完整的人權,要求他們服從父親,卻寄望這種威權家庭能夠培育出有民主素養、獨立思考的公民!
兒童,如同女人,面對的是龐大的家庭∕父權體制。一百年前父權社會說:女人不懂國家大事,不該有投票權;女人很純潔,需要保護以免受害。今天父權社會仍然說同樣的話,對象換了兒童:兒童什麼都不懂,不該有完整權利;兒童很純潔,需要保護以免受害。國小情侶中的女生,則處在性別、年齡雙重身份的交叉點。所以她是純潔再純潔的,受到污染是憾動天地的大事,就像世界末日一樣。
我們不禁要問:這樣的思考,對小女孩公平嗎?
我們承認、而且支持每個人對身體的自主權,絕對為任何對身體自主的侵害反抗到底。但這樣的身體自主權,有沒有包括兒童?當我們大聲要求我們情慾權的同時,卻看到許多媽媽跳出來要保護兒童免於色情
,不讓兒童去接觸不正確的性知識──其實是非官方
的性知識。性知識只有官方版
的才正確。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對身體自主權的剝奪與掌控──只不過這次是女人掌控女人,就像超視主播甜美但嚴厲的聲音一樣。
那小女孩呢?處身性別與年齡的交叉點,承受著雙重的剝奪。沒有人會去追究小男孩到底有沒有完璧?
校長不會檢查他是不是完整?
但小女孩要接受保健室健康檢查,人們在電視畫面上一遍又一遍強調她貞操的重要性
。她的身體自主權被支解了,支解她的是校方、警方、醫生、媒體和社會大眾,每個人都是共犯。
兒童有沒有被污染
不是重點。這甚至是笑話:即使大人不允許,大多數的小女生小男生早就開始探索自己的身體了。沒見識、大驚小怪、無知兼囉哩八唆的是大人。真正的重點是:大人為什麼這麼急著掌控小女孩與小男孩的身體?是不是害怕小女孩和小男孩太早熟悉自己的身體?害怕他們長大後有了身體自主權?
26 歲了,終於出了第一期《女聲》。女聲的製作是一條永無止境的路。不止是目前寫作中的留言板程式而已,還想寫自動訂閱∕退訂處理程式,甚至讀者意見回函、網路投票程式(可以做網路民調)、線上投稿、交友留言板……可以做的有趣事太多了。甚至也許做得好,可以發展成組織,發揮更大的影響力……
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麼地步。也許我不是一個人,而是兩個人。也許不是我們兩個人,而是很多人。女運是一場無止境的奪權鬥爭。當媒體把陳文茜捧成女性主義者,大家也以為那樣就是女性主義者的時候,我就知道,我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。
這一切,都是從《女聲》的發聲做為起點。



